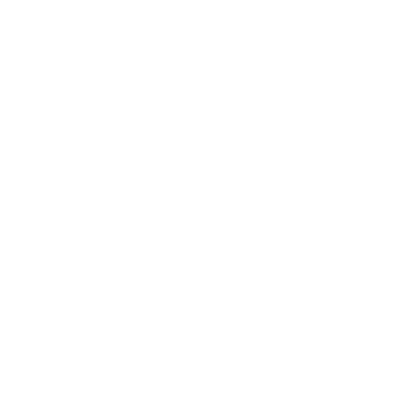《红楼梦》中有一情节:宝玉陪着贾母去烧香还愿,就听说这里有一个叫“王一贴”的道士,很有本事,于是向其索要医治妒妇的方子。
妒者,忌妒也,从女,似是专指女子。
几千年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,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也层出不穷。妒妇就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个族群,她们敢爱敢恨,性格鲜明,为我们了解那一时期女性社会地位、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。
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在帝王身上反映最为突出,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是也,而事实上,又往往会超出这数目,因此工心善妒者,莫甚于宫廷。
骆宾王的一句“掩袖工谗”可算是上郑袖名闻后世了。
楚怀王新宠一美人,郑袖明里向其示好,以表不妒,暗地里看似善意地提醒这个美人,大王说,妹妹哪里都好,就是鼻子长得不尽如人意。美人信以为真,每见王,必以袖掩鼻。怀王不解其意,郑袖趁机进言:她说您身上有臭味。王大怒,下令割掉了美人的鼻子。没了鼻子的美人,自然也就残废了,不存在威胁了。
比起郑袖的割鼻,吕雉和武则天做得更绝。
吕雉与戚夫人在争宠立储的问题上结下了仇恨,刘邦死后,高祖死,吕后断戚夫人手足,去眼毁耳,饮喑药,使居厕中,名曰"人彘"。不仅如此,还让儿子刘盈前来观赏,结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被吓病了。如此狠毒,不光是妒,简直为悍妒了。
有唐一代,除了则天女皇,宫闱之中,可与比肩的还有韦后,《本事诗》记载唐中宗韦后“悍妒”:中宗朝,御史大夫裴谈……妻悍妒,谈畏之如严君。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,中宗渐畏之。不光畏,而且名气在外。一次内宴,伶人演唱《回波词》,词曰:“回波尔时栲栳,怕妇也是大好。外边只有裴谈,内里无过李老。”韦后意色自得,以束帛赐之。这里的李老当然指的就是中宗李显了。怕就怕了,最后,还死在了老婆的手里,算是窝囊之极了。
较之宫廷的勾心斗角,你死我活,公卿士相之家稍微似乎不惨烈些。
《朝野佥载》卷四记载,贞观中,贵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。有一天,阮嵩在厅堂会客,召女奴唱歌,阎氏醋意大发,“披发跳足袒臂,提刀至席,诸客惊散。嵩忙乱之中,匿伏于床下,女奴狼狈而奔”。事后,刺史崔邈作考词责备这位县令:“一妻不能禁止,百姓如何整肃?妻既礼教不修,夫又精神何在?考下。省符解见任。”终因嫉妒而使得丈夫丢官,
《隋唐嘉话》中有房玄龄妻的记载:梁公(按:指房玄龄)夫人至妒,太宗将赐公美人,屡辞不受。帝乃令皇后召夫人,告以媵妾之流,今有常制,且司空年暮,帝欲有所优诏之意。夫人执心不回。帝乃令谓之曰:“若宁不妒而生,宁妒而死?”曰:“妾宁妒而死。”乃遣酌卮酒与之,曰:“若然,可饮此鸩。”一举便尽,无所留难。帝曰:“我尚畏见,何况于玄龄!”她的性格中不仅有妒,更有一种刚烈之气。在最高统治者的强权威严之下,仍然是死不屈从,以生命来进行抗争。在这里体现的已经不是“妒”,而是女性为争取自己的幸福进行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,令人震撼折服,以致最终使得当时的最高权威皇帝也妥协了。
史载独孤皇后性情好妒忌,杨坚后宫中美女如云,但没有谁敢与杨坚同床共寝。直到独孤皇后去世后,杨坚才算是有了自由,宣华夫人陈氏、容华夫人蔡氏等都受到杨坚的宠爱。杨坚开始沉溺于美色而不加节制,由此而得病,在垂危之际对身边人说:“要是皇后还在的话,或许我不会到这样的地步啊。” 看来,像独孤皇后这样的“妻管严”,虽有点不自由却是大有益处。
展开全文
北宋有个文人叫陈季常,《黄冈县志·古迹》谓其“豪侠,好酒,狂放敖世,因怀才不遇,毁衣冠,弃车马。”陈季常爱好歌舞,每当宴客,并有歌女陪酒时,柳氏就用木棍敲打墙壁,把客人骂走。据说东坡先生为此还为好友两肋插刀,指责过柳氏,但柳氏认为苏大文豪没权力干涉她的家事,把他赶走了。苏东坡作了一首题为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》的长诗,其中有这么几句:“龙丘居士亦可怜,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,拄仗落手心茫然。”河东狮吼就这么传了下来。有了柳氏的严格管制,陈季常这个风流士子的歌舞生活才有所收敛。
撇开身份、财富、子嗣这些因素,在这些女子身上,我们也看到了人性的自觉,对爱情、婚姻自由的渴望与追求。她们的身上充满了自由、活泼、奔放的时代气息。
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多妾的婚姻制度,从根本上破坏了家庭男女性关系的平衡,还给家庭带来其它一系列隐患。本来妻子要求丈夫性爱专一,反对多妻多妾,这一合乎人性的正当要求,有利于家庭的稳固,历史却被认为是妇女的不良品德,“女妒为恶之尤,不妒为善为首”,“一不妒足以掩百拙”的说法尽人皆知,甚至连法律也制定了丈夫对嫉妒的妻子可“出之”的条文。
正如黄道周在《性无嫉妒论》的开头提出“时论”的观点:“观夫嫉人有技,穆公著誓于秦中;妒予峨眉,正则行吟于楚泽。是则男子嫉贤,女人妒美,将其性之自然,抑时论之未察乎?”男人贤能被称为俊彦,女人美貌被称为美女,这本是人性所喜爱追求的东西(“贤”“美”),怎么“反得其嫉妒”呢?因为“利欲构于中,而怨恶开其难也。”他认为,“嫉妒生于利欲,而不生于贤美。小人嫉利,而非嫉贤;悍妇妒欲,而非妒美。”因而,利益和宠爱才是引发人们嫉妒的根本原因。为妒妇鸣不平,黄道周可谓第一人了。清代的学者俞正燮更是一位替巾帼执言的大丈夫。他提倡男女平等,写出《节妇说》、《女妻》、《女人称谓贵重》、《出夫》和《妒非妇人恶德论》等不少文章,为深受压迫凌辱的妇女姐妹们向封建传统大唱反调。特别是他的《妒非妇人恶德论》,“妒者,妇人常情”,不但妇人会有,凡人均可能会有。“妒在士君子为恶德,谓女人妒为恶德者非通论也。”另一方面,“买妾而妻不妒,则是忽也,忽则家道坏矣。”如果妻子对丈夫买妾漠然无视,一点也不关心,当然也就不会嫉妒,由于这种漠不关心,家庭之道恰恰会被自己所败坏掉。妻子对丈夫买妾产生嫉妒心理,完全是出于对家庭之道的极大关心,是维持家道的正当行为,无可非议。忌妒恰表现了妻子对这家庭、对丈夫的强烈责任感,她们不愿因为自己的漠然而败坏了自己的家庭,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她们要嫉妒,一定要嫉妒,她们的嫉妒,正是其责任感的表现,因而也是对家庭、社会的一大贡献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